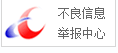握 沙
与汪汪的相识,真心得感谢269。因为都有独处的习惯,常到269去坐坐,不为别的,只是去坐坐。
那日,我们都注意到了对方,他在“十八的鱼缸”的这头,我在那头略一低眉,礼节性的浅笑,算是认识了。我在“共读社”的书架上取下一本《海子诗选》随意地翻看着。说起海子,在当初并不知名。只是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后,被大学同室诗友西川那么一鼓噪,全国人民都知晓了这么个小个子男人,还有着一个不太大众的查姓。不是“渣”男的渣,也不是检查的查。是查(读音为:zhā)。金庸,金大侠也姓查,这是后来大家才知道的事。那时没有“网红”这个说法,知道网络为何物的人,可谓是凤毛麟角,少之又少。
梁平诗人荒儿告诉我:“海子将来一定会进入中国文学史。”
我反问:“何以见得?”
荒儿又说:“你看这句子‘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。’就凭这一句可名流青史。”说完,他便将当时最前卫的纯诗歌杂志《诗歌报》展开来,双手颤抖情绪激动地读了起来:
“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
喂马、劈柴,周游世界
从明天起,关心粮食和蔬菜
我有一所房子,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
从明天起,和每一个亲人通信
告诉他们,我的幸福
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
我将告诉每一个人
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
陌生人,我也为你祝福
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
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
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
我只愿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
读完最后一句,他把书向空中一抛:“日他妈,这才叫诗啊!”
只可惜在当下,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。”这句好诗,被蹂躏得面目全非了。我合上书,不愿再翻一页。
起身,站在窗前细赏小天井里“楼兰的花花”这些个别致的花花草草。粗陋的麻绳网张挂在一面灰旧的墙上,在一个个网结处,疏密有致地悬挂着小小的花盆。多肉,吊兰,野草莓……墙脚一只水缸里还养着睡莲。睡莲是我极喜爱的花,不为别的,只因徐志摩《沙扬娜娜》中那句“不胜凉风的娇羞”。墙角还有一处利用废瓦垒砌的小景,我闭上眼,看见的全是展翅齐飞的黑雁。天刚放晴,有残留的水滴从高处掉下来,“啪——”的一声,更像一滴泪水,在深夜,掉落在一个人的内心。
我的肩头被人轻轻地拍了拍。惊回头,不是别人,正是鱼缸那头的汪汪。
“没什么大不了的事。”汪汪扶了扶下滑的眼镜,在镜片后眨眨眼说。
我轻淡地笑笑,转身,告诉他自己没有跳下去的冲动。他摊开双手,也轻淡地笑笑。我请他同坐,他没有拒绝。
从一杯绿茶谈起,不知怎么就牵扯上了生命的感悟,哲学与思辨,以及生活中许多的无趣与无奈。没有中学生时代的矫情,没有青春期的忧愁与彷徨,也没有中年的焦灼与不安。老景将至反倒多了一些从容与淡定。
楼下大厅里,不知怎么响起了一首老旧的歌声。细听才知是1980代很流行的歌曲《哭沙》。
“谁唱的?”
“黄莺莺。”
我们彼此沉默着,陷入到一种深深的回忆之中。
不知何时,他说起了他现在的生活,被现在的婚姻捆绑得透不过气来。他出身农家,与前任妻子有诸多的问题,分了。他受不了老丈人那或明或暗的轻看与鄙视。而现在的妻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醋坛子”,见不得他与任何女人有所接触。他的朋友圈子越来越小。有个别的老同学甚至愤怒对他吼叫:“你找不到婆娘了?”
出于写作上对人物的敏感,我提示道:“比如说……”
“唉,一言难尽。”他抬眼望着天井里不大的天空,眼里全是空茫。
我不是一个爱多事,爱打听别人隐私的人。浅浅地喝一口茶,心想:如果一个想要的太多,最后很有可能走向事物的反面。她哪能懂得,生活就像握沙。握得越紧漏得越多啊!
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起这些。也许,在这个有点大男孩儿汪汪的心目中,我确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。为什么值得别人信任,我想大概是我在与别人的交往中,终保持着做一个听众的角色定位吧。这是性格决定的,绝不是装出来的那种。守口如瓶,换位思考,理解包容,善解人意。这些算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吧。
别忙着骂我厚颜无耻。汪汪,只是一个化名。也别忙着对号入座。与汪汪命运相似的人应该还有很多,人人都需要倾吐。把自己压抑得太久,就有可能走向抑郁。
望着汪汪远去的背影,看上去不再像往常那样沉重。步履变得如风一般轻快,或许他还哼着小调。如果真哼着小调,那一定是那首由沈庆作词、作曲的《没有想法》。我很喜欢这首歌,所以主观地推想汪汪也一定是在哼这首歌。人,有时就很难客观理性地看待事物,这大概是人类的通病。概莫能外,只是病情轻重而已。
朋友,如果你有想说的故事,我会是你最好的听众。别忘了,我在269。
2019-7-14
我在反思八零年代为何会涌现出那么多优秀的诗作,或许是现在的少了赤诚之心。
也许吧
页:
[1]